来源:胡 泳 陈秋心:中国新媒体25周年——从“信息高速公路”到“未来媒体”的认知跃迁 .《汕头大学学报》,2019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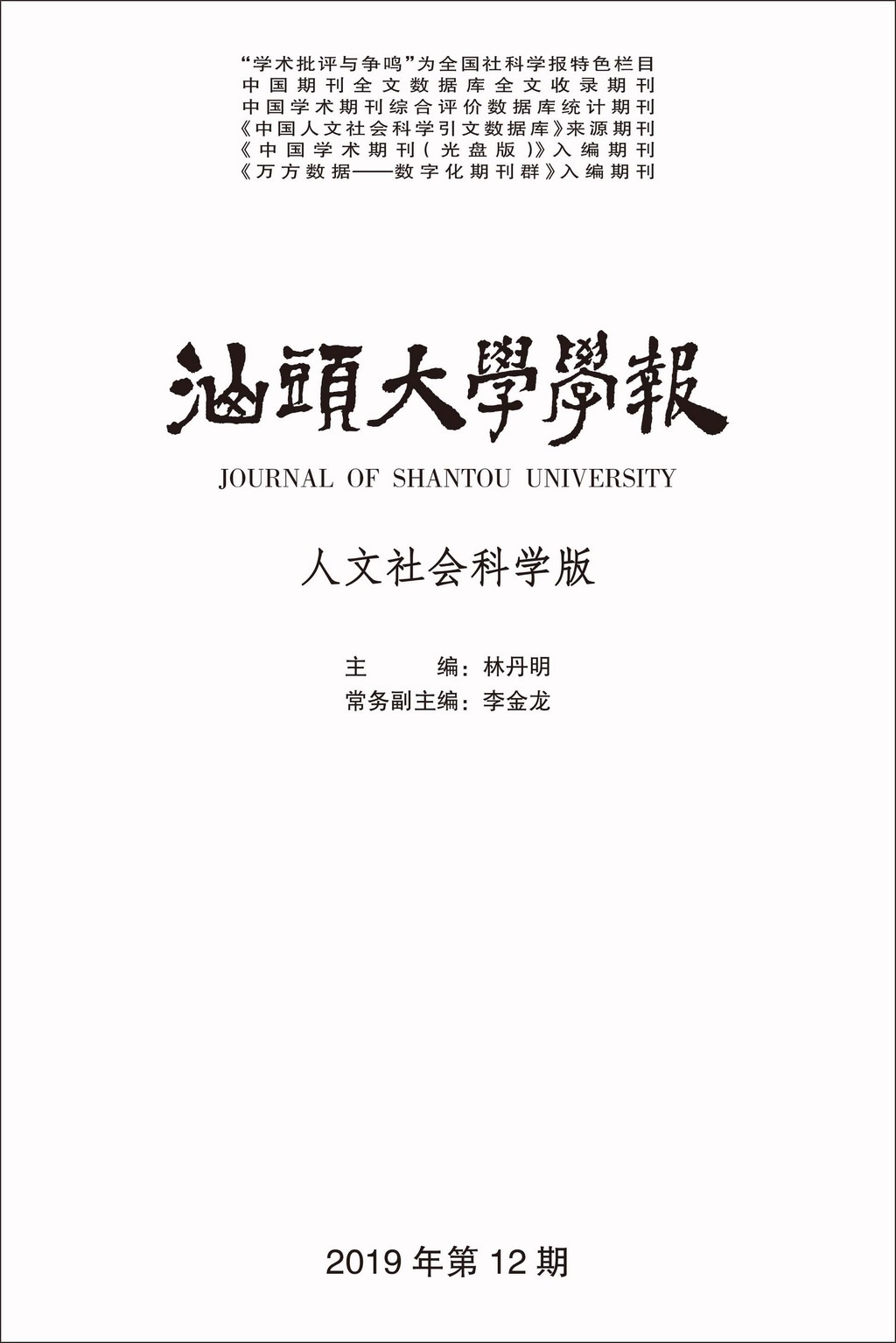
摘 要:“新媒体”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伞形概念。在过去的25年间,它被用于概括互联网进入中国至今层出不穷的衍生技术和应用,其涵义是流动的,每个世代的人都对何为“新”,甚至何为“媒体”有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的多样性折射在语言表达中,即催生了“新媒体”语域中的诸多子概念,包括信息高速公路、第四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移动互联网、智慧媒体、未来媒体等。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子概念总在与技术发展的现实左右互搏、共同演进。通过还原每个概念背后的历史语境,社会、技术和观念的进化逻辑线索清晰可见,这个过程能够启发对人的境况的新思考和对未来技术发展的新认识。
关键词:新媒体 互联网 媒介技术 网络
“新媒体”是一个具有相对性的伞形概念,在过去的25年间,它被用于概括互联网进入中国至今层出不穷的衍生技术和应用,尤其被用来强调互联网开启的与“旧媒体”相对应的范式革命。
在信息通讯领域,当代中国人亲历过不止一次的范式转移,而第一个真正“翻页”的时间节点毫无疑问会落在1994年——这一年中国正式全面接入互联网,宣告了大众传播时代的落幕。但互联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西方产物,无论将其历史上溯到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发明(60余年),还是上溯到埃达•拜伦的计算机理念(150余年),所有的思想积累、软硬件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都与中国没有任何关联。所以1994年的中国几乎是迎面撞上了一个陌生的、全新的事物,全体国人共同进入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并将亲眼目睹它翻天覆地地改变自己的生活。
普通人对“新媒体”的认知,一般围绕着本体(工具应用)、使用(行为)、引发的现象和相应的管理规范展开,而认知的来源则是人们对技术设施、内容、产品(包括应用和服务)的具体感知或者抽象的想象——但复杂的认知过程,包括对新事物的调适、接纳或拒绝,不会被记录下来,只会浓缩为一个阶段性的称呼。于是从“信息高速公路”“第四媒体”开始,“新媒体”在中国的25年衍生出一系列子概念,通过简要还原它们的语境,本文意在呈现中国人对信息技术认知演进的整个过程,以揭示技术和观念的变迁。
一、“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认知的入口
中国刚接入互联网时,“信息高速公路”的概念正火遍全球:1993年美国确立相关计划,成立了以副总统戈尔为首的信息基础设施特别小组,预计投入4000-5000亿美元,在20年内建成信息高速公路。随后日、英、法、加、韩、新加坡等国家纷纷订立类似的发展计划。
所谓“信息高速公路”是指以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为基础,以光导纤维为骨干的高速通道和以电缆、无线传输系统等中低速通道组成的数字化双向大容量信息网络。[1] 而对于刚刚进场的中国而言,这个隐喻般的称呼是关于互联网的第一个符号。1995年中关村南大街上竖起了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一千五百米。”被认为是中国人互联网意识启蒙的第一个象征,而树立这个广告牌的网络代理商“瀛海威”公司的名称即从“Information Highway”音译而来。
“信息高速公路”是一个基于基础设施的称谓,它更容易将人们引向物理形态的想象: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网”主要是通信意义上的,仅仅是将终端连接起来的光纤介质而已。新技术革命无非是让线路的传播速度更快、连接范围更广、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更强,是一场生产力的革命[2],而引起社会生活变革的,是信息时代技术升级导致的传播提速和内容爆炸,而非网络本身的传播特性。
上述观点事后观之显然失之简单,但新媒介技术的来临的确需要依托基础设施。彼时已经落后半拍的中国加快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1995年1月,邮电部电信总局开始在北京、上海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1995年5月,中国电信开始筹建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全国骨干网。1996年1月,该网建成并正式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此时互联网才算是全面进入中国。接下来,不同的行动主体开始进入这个崭新的世界进行尝试和探索,人们的注意力很快从日常生活中难以切身感受到的物理设施转向了丰富多彩的网络内容,对于互联网也逐渐生发了新的理解。
二、从“第四媒体”到“网络媒体”
中国接入互联网后,一场全方位的启蒙开始了。除了政策、文化 等方面的影响, 瀛海威这样的早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也开始积极宣传,并在服务和价格方面展开竞争,刺激了互联网的应用。到1996年,全国的网络用户已达10万之多。
早期用户上网除了收发邮件之外并没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但这种“无聊”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第一批内容生产者就入场了,其中新闻媒体和商业网站是两股主要力量:从1996至1998年,包括人民日报、央视在内的媒体机构大面积“触网”。1998年,全国已有1/7的报纸办起了自己的网络版。[3]而商业网站一边,新浪、网易、搜狐、腾讯“四大门户”很快统一天下,它们与媒体网站既竞争也合作——门户网站虽然模仿美国的商业模式,依靠全球金融资本来扩大业务,但主要产品仍然是资讯、观点,这一点跟大众媒体时代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上网看新闻、看评论仍是普通网民的主要活动。因此,为了获得竞争优势,门户网站每天都需要实时更新大量内容——与具有天然的内容生产优势的媒体及媒体人合作,甚至“挖角”,都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这样的发展态势,使人们顺利成章地将对互联网的理解与既往经验接合起来——此时网络被称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种大众传播媒体,简称“第四媒体”,人们开始目睹“第四媒体”和前三者融合、合作或竞争——这一切都不像“信息高速公路”那样抽象,而是切实发生在眼前、在身边。
然而这一阶段的发展并非“媒体内容上网”那么简单——第四媒体与前三者并不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即便主要提供的仍是资讯和观点,它也有着自己的生产逻辑。仍将媒体网站理解为“电子报”的人很快发现,把报刊内容原样搬到网上意义十分有限,大众媒体从经营模式、财力和效率上都无法和门户网站竞争,“第四媒体“带来的威胁其实远大于希望。
早已有人看到了深植的矛盾。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于1990年代末出版了《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他指出,网络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造成了权力关系的剧烈重组,原有的社会控制与政治再现都因此而改变——将被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大众媒体机构。
但中国此时正身处一场信息技术产业的“大跃进”而无暇他顾——即便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全球信息通讯领域渐入寒冬,中国网络产业也没有停下高歌猛进的步伐。除了越来越多的媒体“上网”外,新浪、搜孤、网易在同一年先后在纳斯达克上市,两年后又先后宣布赢利或停止亏损,使人们看到网络经济的曙光。2003年这三大门户的股价涨幅都在几十倍以上,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或许并不能简单地列在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第四媒体”的称呼逐渐消失,“网络媒体”取而代之。此时大量学术著作问世,开始集中探讨互联网对大众媒体的冲击,后者究竟该如何“转型”,以及“网络媒体”的概念边界该如何确定。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仅从狭义的“媒体”概念出发无法把握互联网的本质。一些看法不惜矫枉过正:互联网是一种“反媒体”,如陈刚指出,“新媒体不是媒体”、“互联网本质上超越了媒体”、“网络是媒介发展的更高阶段,在这个阶段,网络作为媒介(在这里陈刚将媒介和媒体等同)的根本特性是反媒介,即媒介自身的淡化”;[4]而一种看法认为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如喻国明指出,互联网比传统媒体多出一个维度,由此生长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运作空间、价值空间。 [5]但不管如何理解,这样的反思都预示了未来互联网与大众媒体的脱钩。
三、Web 2.0:与“媒体”脱钩
有了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内容市场,2003至2005年,变革的迹象在应用服务领域出现了:论坛、博客、RSS等应用普及,手机终端也开始出现变革,诸如短信、手机报等新媒介形式带来新的想象,它们的影响力在一次次诸如孙志刚案、SARS大型社会突发事件中得以发挥,执行了大众传播时代前所未有的舆论功能,也启发了更多中国网民使用互联网的意识。
2005年,诞生于数年前的博客,终于迎来了大面积普及,“博客中国”获得千万美元风险投资改版为博客网,新浪、腾讯、搜狐等门户网站也纷纷全力打造博客业务。博客成为继门户网站、BBS 之后的第三大网络媒体形态。一部分非常活跃的互联网使用者从BBS 扩散到博客(以新浪博客为主),成为第一批网络意见领袖(俗称“大V”);大量网络事件开始引发关注,网络动员层出不穷,预示着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2008年,中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6]与此同时,终端技术也在飞速跃进,“手机媒体”——短信、彩信、手机电视、WAP门户等风靡全国,一度被称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外的“第五媒体”。虽然在今天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生命力长久的概念,但这个称谓保留了身处变革潮流之中的人们目击新技术一项项涌现时的目眩与激动。2008年,这些新的信息通讯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应用:在汶川地震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网络被广泛运用于信息传递和社会动员,随后和手机媒体都被纳入奥运转播体系。网络新闻在网络应用中跃居第二位,网络视频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影响巨大的、最具发展潜力的主流媒体”。[7]200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视察人民网,在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尽管此时的人们仍在努力将新事物嫁接于过往经验以便于理解,但事实上互联网已经开始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脱钩”——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媒体”,而是一系列技术与实践的组合;它所具有的重构秩序的力量,消解了精英的权威和集中控制的结构,让草根也成为对话者与内容创造者——“Web 2.0”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在内容方面,研究者认为Web 2.0用户所生产的任何数据都可以被称作“微内容”[8],它日益呈现出其作为互联网核心竞争力的价值潜力[9]。一种更深刻的理解认为,Web 2.0所强调的其实不是人与内容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为个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界面、社会纽带。它是个体吸纳与整合社会能量的接收器,同时也是个体能量放大为社会能量的转换器。另一方面,Web 2.0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网络结构的分权,但它并不会带来权力的完全平等。从整体看,Web 2.0指向一个既继承了传统社会生态又具有自己特质的社会生态系统——它是建立在内容之上的社会网络以及文化网络[10]。
在系统特性上,互联网的自组织能力已经得到若干研究的证实,而Web 2.0模式具有更明显的自组织特征。研究者指出,Web 2.0是一个开放的复杂适应系统,在简单的规则约束下,用户广泛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在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去中心化模式下实现了自组织和有序化;从博客知识交流社区的形成,到维基百科的协同组织编辑以及社会化书签产生的分众分类等,无不体现了Web 2.0的信息自组织功能和序化机制[11]。
为什么Web 2.0能够产生如此巨大的变革作用?关键在于此时出现了一个极为庞大、技巧娴熟的网络用户群体,愿意和能够贡献并消化读写网的内容。总体而言,Web 2.0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能和资源主导的体系[12]。
四、移动互联网:靠近互联网的本质
Web 2.0概念的精髓,很快由移动互联网承续下来——以致于如今很多人直接将两者等同为一体。2009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3张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3G时代。一同来临的是硬件终端的突破式革新——智能手机诞生了。二者结合之下,手机上网带宽的瓶颈被打破,智能终端的应用软件模式绕过电信运营商的垄断,集纳了各式各样的开发者,他们提供的丰富应用(Apps)使得上网的娱乐性得到大幅提升,用户的参与面和共享面也进一步扩大。
作为现代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产物,移动互联网包括3个要素:移动终端、移动网络和应用服务[13],它突破了固定互联网的时空限制,不啻为第二次范式革命。有学者认为,手机作为上网终端的革命性在于确立了一种自主的尺度,在任意的时间和地点对内容进行自主阅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线性结构,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人与媒介的互动关系,App所建立的特定的互动关系和内容获取方式,将以前出现的各种媒体形态纳入了一种统一的标准或者说“进入界面”[14]。而新技术时代的众多媒介成为了App的内容,微博、微信、播客、博客等媒介在与App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了彼此更大的价值[15]。
此外,与PC时代的互联网传播相比,移动时代“场景”被置于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彭兰认为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适配。而此时的移动媒体早已不仅是内容媒体,更是关系媒体、服务媒体,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信息流、关系流与服务流的形成与组织[16]。
正是基于移动互联网,自2009年起,微博、微信相继崛起,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成为主导性的“国民级应用”。 2012年8月23日微信推出“公众平台”,使传统上上载于网络的图文内容获得了新的传播模式——从这时起,“自媒体”的称呼日渐风靡。
(一)自媒体
2005年至2006年,中国进入博客发展的高峰,但很少有人高谈阔论“自媒体”。博客造成了一种“全民写作”的现象,随着微博的到来,“全民写作”又变成“全民传播”。草根和精英都欢迎微博,导致微博的风头一时无两。可即便这时还是没有人谈论所谓“自媒体”。
“自媒体”在中国成为关注热点,归功于移动互联网催生的两个因素:一是新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以微信为集大成者——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个人和机构都可以打造一个公众号,群发文字、图片、语音三个类别的内容(后来又增加了视频)。二是UGC为主导的内容生态——随着移动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信息源的多样化,以前门户网站的内容生产模式已经远远落后于众声喧哗、丰富多元的个人媒体平台,相形之下门户网站感叹自己已成为“旧媒体”。出于竞争,各大网站都开始广揽个体内容生产者入怀,催生了中国内容创业的热潮。
自媒体又称个人媒体,其概念可以追溯到英文的“We Media”,早期更多与公民新闻相关联,但在内容创业大潮中商业主义的主导,导致这一概念发生变异,其内在的参与性、公共性元素越来越淡化。[17]人们曾一度对自媒体寄予厚望,例如认为它最大限度地突显了平民的力量、个体的力量,促成传播的个人主义革命,实践着话语民主与传播平等;或是认为自媒体革命能够有效克服传播失灵,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促成政治沟通的改善与政治治理模式的转变[18]。然而也有研究者指出,自媒体存在两大风险:一是被商业买通的风险,二是被权力取缔的风险。这两大风险导致自媒体无法创造乐观主义者设想的基于个人主义的交互式公共领域[19]——微信公众平台的发展轨迹充分证明了这种预测。
(二)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又称“社会化媒体”)是另一个风靡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词汇,但与自媒体的个人化内容生产相比,它倾向于描述人与人的广泛连接和各种规模关系网的建立。
2008 年以来,人们对社交媒体的认识经历了多个阶段:从关注用户贡献内容到凸显Web 2.0与“互动性”,再到发现“关系网络”的重要性,现在则进入新阶段——社交媒体已经从“应用”转向“平台”[20]。 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媒体虽然带有“媒体”二字,但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媒体”的含义,更成为网络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它以互动为基础,以UGC为内容主体,实现了以个人为中心、以关系网络为结构的信息聚合。
令人瞩目的是,社交媒体借助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的融合,把个体传播的社会参与推向了高潮,形成了一个彼此互动的即时的立体传播网络。社会化的媒体和私人媒体的整合,使得局部的信息可能被无限放大,从而在社会动员与力量组织方面产生了巨大的集体效应[21]。这种集体效应,被时为《南方周末》评论员的笑蜀总结为两句话: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
“一个公共舆论场早已经在中国着陆,汇聚着巨量的民间意见,整合着巨量的民间智力资源,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让亿万人同时围观,让亿万人同时参与,让亿万人默默做出判断和选择的空间。”
社交媒体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博客转帖、推特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理性的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地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22]。
但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也带来很多忧虑。有人认为在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两方面,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具备建构公共空间的优势条件。然而,网络商业主义、集体无意识和注意力承载力这三方面因素的困扰,严重影响了微博等社交媒体对舆论公共空间的积极建构[23]。也有人指出,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的兴起,并没有按照很多人预期的那样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度,而是让人们的政治参与度下降了。因为社交媒体“熟人圈”的人际传播特点,在于引发传播的各方保持相互关注或保持友好关系,而非破坏这种关系。人们担心打破与熟人圈或准熟人圈的平衡和友好关系而保持沉默,甚至向相反观点妥协[24]。
四、未来媒体:智媒时代的来临
基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范式革命,一些学者对互联网分期有了新认识: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本特征,观察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社会应用,会发现一个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交叠发生的演进线路图:Web 1.0时代为“内容传播-信息搜索”;Web 2.0时代为“个体创造-群体协作”;而接下来一定会有Web 3.0时代,即“万物感知-智慧控制”[25]。
2010年以后,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5G、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下,信息通讯领域出现了智能化趋势,揭开了“智媒时代”的序幕。媒体智能化的主要表现为万物皆媒、人机共生[26]——很明显,在这样一个称谓中,“媒体”早已脱离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定义,转向更宽泛、更丰富的“媒介”意涵,在某种程度上说,未来“媒介”的边界甚至超越了信息通信的范畴。
狭义上说,媒介指起中介作用的空间或中介物,可以是材料、工具、支持等很具体的东西,宽泛地讲媒介甚至可以包括某种社会实践[27]。 而人本身既可以是实践的主体,也可以变为一种实践的媒介;甚至人的身体和意识甚至在未来可能分离,分别独立承担“媒介”的功能。
一种共识是,智能化将成为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智媒”时代,需要崭新的媒介产品,专为多设备、多屏幕世界而设。例如,VR技术的“3I”核心特征,即沉浸(Immersion)、交互(Interaction)和想象(Imagination),带领使用者以第一视角近乎真实地感知事件发生时的现场,构成一种全新的讲故事方式[28]。
从具体形态上看,物联网与可穿戴设备是未来的传播媒介的代表,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感知情境的计算,永远跟一个人身处的情境相关,所以,这种计算混合了对位置的感知、对身份的管理。目前这种感知与管理同手机的信息采集和用户的社交网络联系等要素还没有充分融合。如果将来所有这些要素都充分互联,并且可以互操作,那么就可以基于用户的需要、用户做过的事情、用户所在的地方乃至用户正在做的事情产生更有趣的服务[29]。
亲证了二十多年来信息通讯技术的惊人变革,人们已经不惧怕对即将到来的新媒发挥最丰富的想象——不管是人工智能、区块链还是沉浸式媒体,通通被归入“未来媒体”的概念之下,由此进一步思考新闻生产方式、劳动分工、家庭结构、亲密关系乃至人的存在本身将会收获哪些裨益、又将经历何种挑战。总体而言,未来媒体并不是“媒体”,或者说并不是简单的介质,而是脱离当下现实的依凭,直接想象未来彼岸的一切可能性——“未来媒体不是向大家展现未来的媒体应该是什么样的,而是对传统传播思维方式的颠覆和变革。”[30]
五、讨论与反思
从“信息高速公路”到“未来媒体”,回望来路,短短二十余年里,信息通讯技术和人们对技术的理解和想象都经历了多次跃迁——尽管理解总是滞后于技术一步,它们却记录了中国面临新事物时震惊、好奇、理解、调适的过程,期间还有互联网与大众媒体之间的博弈。今天,整个国家终于得以站在时代前沿畅想未来。
人在试图理解新事物时总是先借助已拥有的东西和过去的经验——国人一开始将新的信息技术等同于一个独立的、与大众媒体机构并列的存在,所以总要在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继续编号,才有“第四媒体”“第五媒体”的说法。但飞速变化的技术现实很快反驳了这种简单的理解——首先互联网和手机都不是能大众媒体相同性质的存在,它们很快演化为现代人生存的基本场所与工具,成为“遍在”的、一切活动的底层逻辑。其次,互联网和手机早已合二为一,近乎演变为现代人须臾不可脱离的“外部器官”。第三,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本身就有局限,最初将其理解为基础设施,后来将其理解为内容网,21世纪之后才发现它是关系网、资源网、渠道网……而当互联网转变为移动互联网之后,其影响力几乎完全重构了现代社会生活秩序。
好在人总是能通过不断的反思来把握进化的逻辑。经历了“第四媒体”的想象力挫败之后,国人在展望未来时调整了思维,释放了想象,急切盼望着开启再一次的范式革命,进入“互联网的下半场”。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内涵也急剧扩大。90年代的“媒体”仅指大众传媒,但这个狭义的理解已是明日黄花,今天人们面临的是“万物皆媒”的处境,甚至要提前忧虑未来媒介技术对人的异化和取代——中国当下已经进入了一个对技术非常敏感的时期,思考媒介技术和我们未来生活的走向不再是精英的专利,而是成为每个普通人的日常。
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在回溯过程中并没有使用“新媒体”一词,原因正在于其涵义的不固定——只是一个从自我出发、归纳自身所处时代技术的笼统总称。
有关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外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聚焦于新媒体的媒体形态和技术特性,另一类则认为对新媒体的理解要超越对媒体技术形态的关注,研究媒体技术与人类行为及社会结构的交互影响[31]。但不管采用哪种进路,只要有人试图赋予“新媒体”一词确定的涵义,通常会掉入时间的陷阱——若干年后回望,那个定义很有可能已经充满了陈旧的年代感,无法准确地概括当下丰茂的、鲜活的技术现实。正如潘忠党所批评的那样,不加辨析地使用“新媒体”一词,背后包含着谬误:
“不同的生命体验通常对应着不同的历史时间点,也对应了不同的媒介技术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危险:这样的思维和逻辑本身包含了一种潜在的认知谬误(cognitive fallacy),即“历史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的局限性。”[32]
而作为解决方案,潘忠党本人试图以特性来定义边界——这种做法并不鲜见。数字化(digital) 和网络(network)这两项最为基本的特征就经常被用于区分当下的“新”“旧”媒体[33][34],但问题在于这两个标准因太过基础而显得大而无当,只能用于区分不同范式。当然,也有人使用超文本、多媒体、互动性描述“新媒体”[35],但仍不够全面。而潘忠党通过亲身观察和博采众长,提出了三类十三项媒介可供性(如表1)来区分媒介本体的新与旧——在各个方向可供性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本文十分赞许这种提高抽象性的努力,但认为在讨论具体问题时需要就事论事——明确自己的讨论对象,使用它特有的名称,例如使用“社交媒体”“智慧媒体”或“自媒体”,而不要总试图使用全称、概括普遍规律,效果可能会更好。
表1. 媒介可供性的构成

出于同样的考虑,本文也避免使用“传统媒体”一词,因为这显然是跟“新媒体”相对的一个概念,带有同样的不确定性——“传统”是谁的传统?对于现存世代而言,大众媒体是上一个技术范式遗留的“传统”(英文中将“传统媒体”称为legacy media,更带有“濒临灭绝”的意味),但若干年后,论坛、门户网站、博客甚至微博微信都可能成为下一代人的“传统”。
而至于“新”“旧”媒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可能并不存在人们惯常以为的“媒介替代”,即便是“传统媒体”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衰亡与落后。在现实个案中,很少看到大众媒体被完全替代的例子,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同媒介形态之间要么合作,要么竞争,要么融合。新旧媒体因此不是壁垒森严的两个系统,而是同属一个“扩展了的媒介生态体系”(enlarged media ecology)[36]。
六.总结
总而言之,近年来通信领域的技术发展波澜壮阔,无论是积累、改良型创新还是突破、革命性创新,都与社会力量交织演化,共同构造了我们当下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一代代人对于通信技术的认知也在不断进化——本文认为对于这种认知变迁的审视是必要的,因为其中能够折射技术的演进路径,也能反映社会变迁。
历经25年,当我们发现互联网终于由工具的层面、实践的层面抵达了制度形式的层面,最重要的是回到原点,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是互联网?——但在这个核心问题背后还有无数问题:我们该如何审视日常世界中这个无处不在和熟稔无比的事物?互联网能做什么,在它能做的事情当中,哪些是崭新的?它又引发了什么新的伦理、社会和政治能力?它使得什么东西过时,或成为问题,甚至变得不可能?随着我们周围的世界不断重组,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的那个“社会-技术”组合,挑战了许多构成我们当下时空的熟悉假设以及想象。
作为网络传播研究者,我们反对把“互联网”视为一个单一的实体,也尽量避免将其笼统称为“新媒体”,而是将其看做一种时有不同的技术、平台、行为和话语的集合,它们与社会互相激荡,共同演变。至于对未来媒介技术的想象,我们可能既需要新的价值论(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也需要新的认识论(关于知识和科学的理论)。
最终,所有的思考一定会达到一个层面:在充分联网的环境下,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构成人的定义?什么叫做人?什么叫做人性?这其实是互联网文明的可能性问题,最终的含义是人的可能性问题。
作者简介:胡 泳,男,湖南嘉禾人,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秋心,女,河南信阳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
参考文献:
[1] 李斯颐. 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技术与大众传播[J]. 国际新闻界, 1995(1).
[2] 居延安. 谈谈信息革命[J]. 新闻大学, 1984(2).
[3] 彭兰. 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64.
[4] 陈刚. 新媒体时代营销传播的有关问题探析[J]. 国际新闻界, 2007(9).
[5] 喻国明. 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J]. 南方电视学刊, 2015(1).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80719[20191221].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0906/P020120709345337342613.doc.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北京: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80719[20191221].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0906/P020120709345337342613.doc.
[8] 喻国明. 微内容的聚合与开发:网络媒体内容生产的技术关键[J]. 网络传播, 2006(10).
[9] 汤雪梅. 微内容对互联网的价值重构[J]. 国际新闻界, 2006(10).
[10] 彭兰. Web 2.0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社会意义[J], 国际新闻界, 2007(10).
[11] 李鹏. Web 2.0环境中用户生成内容的自组织[J]. 图书情报工作, 2012 (16).
[12] 胡泳. 共有媒体初探[J]. 现代传播, 2007(5).
[13] 吴吉义, 李文娟, 黄剑平. 移动互联网研究综述[J].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 2015(1).
[14] 王建磊. App:认识新媒体的一个崭新视角[J]. 新闻记者, 2011(11).
[15] 邓逸钰. App的媒介使命演变[J]. 现代传播, 2014(3).
[16] 彭兰. 移动化、智能化技术趋势下新闻生产的再定义[J]. 新闻记者, 2015(1).
[17] 於红梅. 从“We Media”到“自媒体”——对一个概念的知识考古[J]. 新闻记者, 2017(12).
[18] 潘祥辉. 对自媒体革命的媒介社会学解读[J]. 当代传播, 2011(6).
[19] 胡泳. 自媒体的探索与冒险[J]. 南方传媒研究, 2014(47).
[20] 田丽, 胡璇. 社会化媒体概念的起源与发展[J]. 新闻与写作, 2013(9).
[21] 任孟山, 朱振明. 试论伊朗“Twitter革命”中社会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 国际新闻界, 2009(9).
[22] 胡泳. 围观与见证的政治[J]. 文化纵横, 2013(4).
[23] 袁靖华. 微博的理想与现实——兼论社交媒体建构公共空间的三大困扰因素[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
[24] 陈力丹, 谭思宇, 宋佳益. 社交媒体减弱政治参与——“沉默螺旋”假说的再研究[J]. 编辑之友, 2015(5).
[25] 高钢. 物联网和Web 3.0: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的交叠演进[J]. 国际新闻界, 2010(2).
[26] 彭兰. 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J]. 国际新闻界, 2016(11).
[27] 胡泳. 理解麦克卢汉[J]. 国际新闻界, 2019(01).
[28] 喻国明, 谌椿, 王佳宁. VR(虚拟现实)作为新媒介的新闻样态考察[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29] 胡泳. 未来的传播媒介:物联网与可穿戴设备[J]. 新闻与写作, 2016(11).
[30] 李彪. 未来媒体视域下媒体融合空间转向与产业重构[J]. 编辑之友, 2018(3).
[31] 毕晓梅. 国外新媒体研究溯源[J]. 国外社会科学, 2011(3).
[32] 潘忠党, 刘于思. 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7:19.
[33] Manovich, L.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M]. MIT Press, 2001.
[34] Jensen, K. B. Media convergence: the three degrees of network,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10.
[35] 胡泳.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6] 邱林川, 陈韬文. 迈向新媒体事件研究[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9(09).

 红包分享
红包分享 钱包管理
钱包管理


